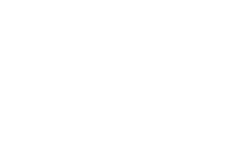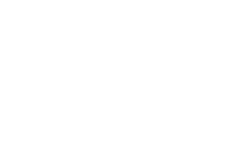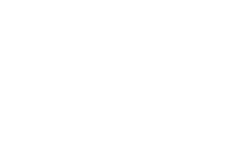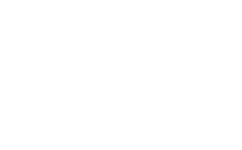故乡卧在皖北。村庄四周被界沟镶着,嵌着参差的草木虫鸟。冬天,它是一副清峻的水墨画。春天,柳绿桃红梨白菜花黄,不动一笔、不着一色,它就变成一副迤逦的水粉画。
祖先一定是归隐的雅士,如此设置村庄,世代都生活在田园画卷里。通往村庄的路就一条,但春天不走寻常路。当阳光日益炽热,东风逐渐暖醺,界沟边的金柳便垂钓起春天。于是,某一夜,春雨如酥,柳条往村庄里一甩——第二天,到处都是活灵活现的春天。
柳树引路,迎来送往,每一个枝桠都妙笔生花: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孩子们蹦蹦跳跳来了。他们才不管池塘春草梦,只顾采撷花草,装饰着小皴脸。有的攀上柳树,折一些柳枝,做成柳哨。一边悠然地吹,一边编织柳帽、柳裙。
燕子嘁嘁喳喳来了。那身干净利落的燕尾服,我们羡煞了整个童年。黄鹂站在朝南的树枝上,像个帝王,一个人歌舞升平。喜鹊总没玩没了,言多必失,巢建得一塌糊涂……有时,我们会攀上树,串门。黄鹂倒还客气,黑乌秋和喜鹊却不领情,尖爪利喙齐上,直接轰你出门。
曾因一个雏鸟,我被黑乌秋全村封杀,连忠实的黄狗,也不敢替我出头。直到父亲完鸟归巢,我才被解禁。以后,我再没招惹过它们。父亲说,要是有人偷我,他也会拼命。我没想到,他这般爱我?平时教训我也蛮拼的!但我依稀懂得,鸟也有亲情,也父子情深。
桃花一树一树的开了。开得璀璨,开得决绝,开得没有退路。和其他树不同,桃树是开完花才长叶。有些像母亲,总是把最好的先拿给父亲和孩子,最后才是自己。母亲是女神,执著地守着家,从繁华开到荼蘼,依旧笑春风。
乡俗说,桃树辟邪。那守着院门口的桃树,也是桃符——父亲是上联,母亲是下联。
桃花红菜花黄,春天也到了黄花闺女的年纪。寂寥一冬的菜园,热闹起来。春韭抹掉草木灰,水嫩而茁壮。荠菜不请自到,撵着阳光长。泥土下猫冬的萝卜、白菜,焕然一新,对着春风贴花黄。蜜蜂来了,蝴蝶来了,恍若一眨眼,就孩子一样养不住了,该谈婚论嫁了。
村庄最高的树是椿树,长在各家院落里,这样就能“怀抱春”。当椿树的芽苞像马鬃般散开时,春天也驰到尽头。所以,椿树还被唤作马蹄子树,寓意白驹过隙;所以,春天消逝于院落,马作的卢飞快。村人不怕,不急,他们坚信,就像出去耍的娃,早晚还会回来。
开云平台注册网站 春天住在故乡的村庄里,那块土地上,有未完的故事;那片泥土下,有绵延的根须;那个院落里,有永恒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