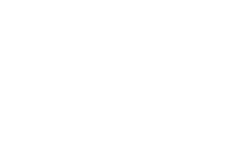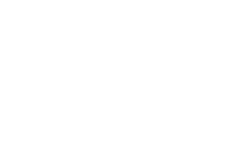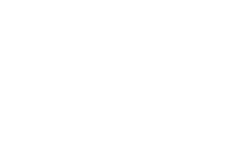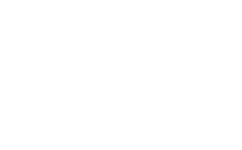花 生 情 结
张轩朝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分农产品是按劳力来的。我母亲过世早,父亲在学校教书,户口不在村里,奶奶已超过劳动年龄,因此,家里没有劳力,这要被村里人看低的,虽然自己着装卫生方面稍优,别人的眼光,至多把我看成一个干净的次等人,这到年底分农产时尤为明显。快过年了,别的家庭大筐挑小筐扛,分到我家,像抓中药,花生、大豆、棉花、糯米,每样一点点,拿回家,不够一次饱,吃过等于没吃,连瘾都过不足,咂咂舌头,梦一样就忘了啥味,留下无穷无尽的慢性饥饿症一天天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能吃的东西少,生产队种的稻、豆、棉、麻都无法即食,又不能像牛那样吃田埂上的草,除了忍,再没别的办法。
但作物中有一样能吃,那就是花生。
花生收获的季节是在七月。每到这时节,村口通往花生地的土路上,夕阳的余晖从河对岸的山头热热地撇过来,汗水味搅和着鲜花生水润润的芳香,飘在黄昏的空中,纠缠人的胃口。满身泥土的大人们挑着花生从土路上陆续归来,似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早在村口的屋角等候,大热的天,几乎每个孩子都穿着大口袋的冬装,额头沁着汗,眼睛巴巴地往土路上搜寻自己父母的身影,临近了,牛犊般唤一声,父亲或母亲便神神秘秘地踅过去,放下担子,贼贼地察一眼身后,迅速从筐里大把抓起泥湿湿的花生往孩子口袋填,直到将所有口袋装得鼓鼓,再装作没事样挑起担子往生产队的仓库去。我小时候嘴馋,看到别人吃东西,无论什么,立马嘴咽生涎,肚子特别饿,觉得那东西一定好吃且最适合我吃。作为家里没有劳力的边缘人,此时的我,虽馋得难受,也只能站在稍远的地方,羡慕地咽口水。
这样的“腐败”是个公开的秘密,连生产队队长也不例外。这段时间里,每家每户每日都有美味花生吃,大人们嘴角挂着嚼余的白色花生浆液,孩子们不太会讲卫生,吃得嘴脸是泥,拉肚子便难免了。因此,花生收获的季节,是村里人拉肚子的季节。每每看到同伴们憋得脸色发紫地往厕所冲,摔厕所门的“嘭”声与不雅的“哗”声几乎同时响起,我便羡慕得发慌,想象那过足花生瘾后的滋味一定赳壮,自己啥时候也能吃到嘴脸是泥并拉肚子就幸福了,那往厕所疾奔的模样,是一种身份和享受。我奶奶大概看出我的馋,教导我说:“肚是空布袋,越吃越胀开”, 我觉得自己的肚子是在某个时候吃得太多给撑大了,一日三餐,菜蔬糙米,吃的时候觉得饱,稍一转悠肚子就空,午饭和晚饭前的饿至今还有余怕。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被花生补到拉肚子,我呢,苦命到连眼前美味都只能臆当画饼,这缺憾,等我长大当了社员,一定狠狠补回来。
然而,到了我懂得拉肚子会不好受的时候,饱餐一顿花生的愿望已成为记忆中的烟云渐渐淡去,只留一段落寞的开云体育娱乐ac米兰赞助商官方入口,浮雕般定格在童年的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