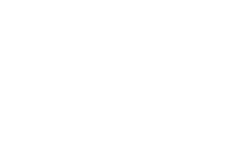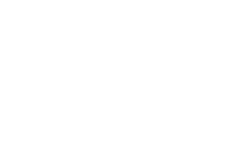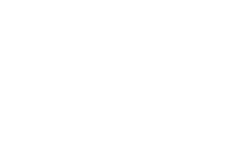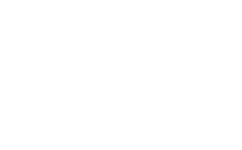毫无疑问,你一步踩进洞庭湖的冬天了。
寒冷、干涩的空气穿透着肌骨。退水后干涸的湖底,龟裂的扳块,让脚扳硬痛。抬眼望,灰白的云厚厚地铺陈在天空,压抑着眼帘。草丛与树木,落叶和残花的萎谢枯黄,收缩中渗透出游丝般的泥腥味。
几块青草,在灰褐的土地上,散发着幽亮;几丛菊花,风中摇晃,在灰蓝的半空,残存暗黄;一湾溪流,在稀疏的芦苇杆旁,迷雾般地徘徊。偶尔,一蓬红枫,几只飞鸟,从眼前闪过。
它们似乎在告诉:肃杀的冬天,总有不屈与抗争,冬天的直裸,总是伴着灵魂的呐喊与骠悍。可呐喊里不免有英雄的无奈,骠悍中难逃暮年的悲哀,走近洞庭湖的冬天,你看到是一幅苍凉的悲壮,你触摸到的是一番迟重的感慨。
本没有路的沼泽,干涸后被人走出的无数路迹,让我们无需选择的选择,在一条路又一条路上行进,向洞庭平畴的远方,朝天与地的连接处走去。
地,似乎越走越平坦、厚实而丰满,天,仿若愈走愈开阔、空旷而明亮。
芦苇成堆成堆地象房舍似地静立着,把大地夹成纵横的纤陌;浅白的云絮一片一片地游离,把天空涌细浪层层的湖滩;一池湖水,跟着隐约的阳光,时不时地或明或暗。湖边的草,仿佛并不知冬之寒冷,泛着青绿。草滩上的芦杆,似乎不理睬冬之萧索,黄中透红,顶上白晃晃的芦花在风中招摇。
这景象,这风光,这情致,突然得有点神秘,讶异得有点惊颤!越走进冬天,冬之景象竟迷一样地渐行渐远;越向洞庭的深处,春色竟象芦花似地愈见愈浓。
当阳光逆着杨树的枝条,阴影的周围泛着眩目的光晕;当浅红的芦杆密影在光色中穿梭;当芦花银絮般地飘摇,忽而明灭;当一阵清风拂衣而来。你闻到那泥土潮润的腥膻与芦草的幽香的青涩;一声鸟鸣,你看到它划过光晕,象慧星般飘过;一种神秘的崇敬感悴不防的充塞心胸,弥漫全身。
恍惚如梦的神灵在拽引,徒然跌入似海的芦苇。一条小道宛如水痕,沿着两旁透着赭色的齐刷刷的芦苇,勃勃曼曼地流逝过去。
拐过弯,一线明亮如月的河水,笔直地伸展,消逝在视野的尽头。两岸空旷平坦的青绿草滩与高旷的蓝天遥遥相对。白云浮游似的芦花,闪着或银或金的光斑,泛着柔柔的色泽,透折晶亮的质感。仰头听那冬雁飞过,侧耳都是湖风荡漾,时不时几只黑色带着白花点的小鸟,在半空中飞鸣,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一刹间,你会恍惚这不是凡间之地,这只能是一片梦中的圣境。清纯,透明而又迷蒙。你站在此间,仿佛也变成了一个高贵、神圣、清雅之人!你会感谢命运之神让你在寒冽的冬季开阳之际,有福份看到这份难以寻觅的,隐约在空旷而浩渺的洞庭天地里光影。
你难以相信荒芜空漠的冬天,竟蕴藏着如此明丽、浩然的春色;你无法明白,冬天的肃杀为何竟有如此蓬勃、高扬的春意;你都不敢,将忆念的春景与此刻的春光对比。
不是春,胜似春!
冬天的春色,脱尽了春的稚气与喧嚣,远离了春的骚动与盲撞,作别了春的纷繁与紊乱,它成熟理性,象芦杆,通透生命的内质,直抵灵魂的深处,象芦花,在阳光下飘逸,享受纯然清丽的快感。更象具有思想的芦苇,让春、夏、秋充塞芦管,一并在冬季褐色的苍桑中绽开穿透天地,温暖心间的春色光芒。
草创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