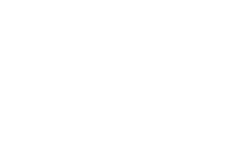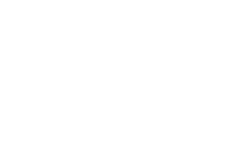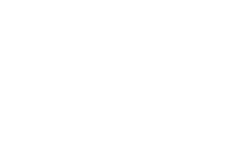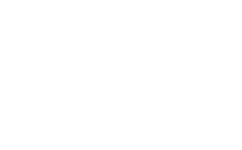他好象上了车,是超过了报废期的长途面包客车。
看不清人,只有一些人影在走动与晃荡;也看不到路,只有人的上下颠簸。可能是走在一节泥石的乡下路上。人声嘈杂,但他又听不到丁点声音。车走得象船样的摇晃。
模糊中,似乎就是船,恍惚中在长江三峡的大坝的船闸里,两边是高于十来丈的笔直的灰白的水泥壁。水流平平的托走船行走。前面两根象是麻绳吊着一个巨大的黑门,缓缓上升,绳仿佛随时要断似地,又发出钢丝断裂的吱吱声。车内没有别的人,只有他。不知怎,他变成了司机,坐在驾驶位上,眼睁睁地看着那要断了的牵着闸门的绳索,没有丝毫害怕。
到了象街河口那样的码头,景象是五十年代即繁忙又破败的样子,衣衫褴褛的脚夫子扛着扁担三五成堆的,还有一些穿绸缎和卡其布的人提着竹簏柳滕的箱子在船的跳扳上,上上下下。几条木扳凑合的小舟停在一些机帆船旁,远处水面上两艘拖沙的船缓缓而过。
从船上跳下来,就到了小卖铺前,铺面比街面低多了,似乎是地窖口子。一个木架的柜台,安着玻璃片窗,里面是香烟和小零食,还有一种车糖时勾做的鸡与龙的造型。柜台里露出曾经是他办公室主任的苏的半边脸来,他知道他的脸本来就很小,此时被告柜台遮盖得只剩下窄窄地两条黑线。他还是认出来了。好象事先约好的,苏说“快去找他。”他的说的他,过去也是他的下级,不过后来又当过一阵他的临时上级,现在他正要找他去报销发票。奇怪的事是他老兄也露出了一张整脸,没有表情也没有说话,只是痴痴地望着他,他也没有任何奇怪的反应,就走了。
他在敲门,这门同样也比地面低,房子象是个地下室改造的。“来了,来了!”门吱地一声,
在他听来象是仕炮的声音。陈氏出来了,胖胖的脸上,头发比以前卷曲多了,站在门里面一边身子还在披衣服,“刚睡,就吵醒了!”话音很重,但脸神却一点也没有生气的痕迹。为了让两个人都站在门前,门又吱地仕了一下打得更开,里面乱七八糟的的白晃晃的木材堆得到个都是,床都埋在木堆里,陈氏似乎刚从柴堆里爬出来。
不知为何到了屋顶上,踩着屋檐似的。屋顶斜坡,一块薄木扳溜溜滑滑,踩得吱嚓嚓地响,象马上要踩埸。这回他真害怕了,站在那里一步也不敢挪。伸头朝下望,离地还有很高很高,仿佛是站在一个百米的建筑物上,隐隐地看到了远处的船码头,看到那灰褐灰褐江水。他蹲下身子,发现自己的脚踏在木头的尖顶上,没有刺脚的感觉,只觉得风将身子吹得遥晃起来。他试着探了下准备沿屋檐下去,可刚一伸脚,就被一阵凉风吹得缩回。
屋顶对面有一个四方小窗,窗子里时现时隐一个奇异的笑脸,是一种疯人院里常见的笑脸。又象巴黎圣母院钟搂上闪现的黑影。他身旁不知何时站了一位年纪蛮大的人,手里却拿着弹弓,一把钢制涂着黄军用色的弹弓。“喂!黄鼠狼!”不知谁叫,他转向那屋顶对面的窗口,一只象松鼠,又象四脚蛇,身上闪着金黄与鲜绿交叉的花纹,好象一束手电光,又似乎是一束带有灰尘的阳光直射在它身上,随着它的在那神秘窗口人手上扭动而变幻着奇异怪状的图案。
“嘎!”的一声,似乎子弹飞出去了,黄鼠狼及人倏地消逝了。
他为何躺下来,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躺了就躺了,还舒服些。躺在一个园弧形的竹椅上,一边跷跷板似的,一边听过去下属一个分公司经理的诉说,这人很久不见了,一段时间象水汽蒸发似的,没留下一点水渍印子。这时不知是如何冒出来的,他好象是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说是他去过一个洗脚城留下的,那纸在他眼前荡了几下,又躲也似的藏到经理的身后,象一个挺羞涩的小孩。他是为了她来扯皮的,说是那一次后,有了,现在她把孩子带得好大了,做了亲子鉴定。
过去的事好象从来没有这事。他没有那爱好,他是有品位的人,不会到那种下三乱的地方去干作呕的勾当,做亲子鉴定?!没有他的如何鉴定,起码常识都没有,就来唬人!
但他分明又看到那经理的纸条上,自己常常签字的熟悉的字体,尤其他看到那富有特色的勾,是近乎园圈的勾。难道自己?!他也弄不明白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喂!干嘛?睡不着,就起来,哼莫里!”
他醒了,窗外已有的白色,于是他披衣下床。
草创小说《失去童话时代》的断片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晨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