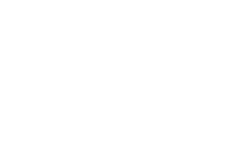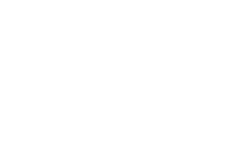早年辰光,弄堂里常有肩挑剃头挑子的剃头匠,走街串巷,服务弄堂居民。不知何时,剃头匠鸟枪换炮,紧傍老虎灶,搭建一爿“滚地笼”的小剃头店。
剃头店虽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逼仄的店内,一张老式铸铁理发修面椅锈迹斑驳,那是从美发店里淘来的。黄色木框大镜子立在窄窄的木台面上,手动推子、折叠剃刀、剪子、梳子闲散地躺着。墙上贴着几张漂亮的电影明星的彩照,为小店增添了一些鲜亮的色彩。屋顶糊满旧报纸,正中央悬着一只原色难辨的吊扇,一盏钨丝灯泡发着昏黄的光。
来剃头的多是弄堂的居民,清一色男性。天长日久,他对每位顾客的需求熟稔于心,而每位顾客也都习惯了他的手艺。
剃头匠严格恪守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技艺,剃头、修面、掏耳朵、剪鼻毛、清眼目、修胡须以及头、面、颈肩部按摩,一样都不能少。而修面更是剃头匠的绝活,客人坐在吱吱作响的理发椅上,剃头匠轻轻一提,修面椅就放倒了。一块滚烫的热毛巾焐在客人脸上,片刻取下,再用蘸满肥皂沫的毛刷涂抹在客人两鬓及胡须上,师傅取出闪着寒光的剃刀,在油亮的荡刀布上来回荡磨,剃头店内“唰唰”的清音在跳跃,师傅仿佛成了磨刀霍霍上战场的战士。“磨刀要轻,荡刀要重,刀磨得好,修面时才能做到随心所欲。”这是剃头匠的诀窍。剃刀荡好,修面开始,他左手食指和拇指轻轻撑开客人面部毛孔,刀锋如行云流水,刀片在两指间轻松滑动,发出“沙沙”的响声,边刮边用手指摩挲,额头、眉心、眼皮、耳朵,全用剃刀操持。他就像玩催眠术的大师,鼓掌间把客人送入了梦乡。
头发绾成齐整的发髻,一袭鲜艳的棉麻衣裤,春风满面的阿婆走进剃头店,盛邀剃头匠为孙儿剃满月头。剃头匠把剃刀和梳子用酒精认真消毒,然后用红布头把剃头家什包裹好,挟在腋下上门去剃满月头了。
别小瞧满月头,这是一个精细活。头还没剃,婴儿就哭,一哭头就乱动,这也难为剃头匠了,他一边剃头,一边轻轻哼起了扬州小调:“乖乖的宝呀,剃头不要哭呀,剃下的头发做支笔呀,十八岁以后中状元呀”,婴儿在小调声中沉沉睡去,满月头也就剃完了。剃完头,剃头匠嘴里嘀咕着,轻拍几下婴儿后脑勺,家人会心的笑了,大家猜想是那句俚语“新剃头,不打三记瘌痢头。”剃下的头发剃头匠仔细收拢,放入他带来的小红布袋内,黄丝线一扎,交到阿婆手中,叮嘱道:胎发来自父母,不要丢弃,仔细珍藏。丰盛热闹的满月宴开始了,剃头匠也成了座上客。在一声声祝福中,推杯把盏,剃头匠也幸福的分享主家添孙的快乐。
剃头匠既为新生儿剃满月头,也为终老者送去暖心的服务。弄堂里老人去世,丧家来请剃头匠上门服务。他换一身青布衣裤,剃头工具包在白布头里,神色肃穆凝重进入丧家。
一盆清水洗净双手,开始“一条龙“服务,仔细修剪头发,精心修面,手指摩挲中,半开的眼皮轻轻合上,鼻毛修剪,指甲剪短,剃头匠熟稔而轻柔地打理着。最后,剃头匠打开一个鸭蛋型的小盒,散发着淡淡的茉莉花香,那是扬州小姑娘喜欢的粉饼。剃头匠用粉饼在逝者脸上精心补妆,剃头匠成了美容师,不一会儿,大功告成。逝者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润,安详宁静,栩栩如生,逝者仿佛沉沉入睡。就像做了一项大工程,剃头匠满头大汗的长长吐了一口气,低头轻轻说了一句:干干净净来,清清爽爽去。
夏日午后,剃头匠正坐在长凳上打瞌睡。一位头顶草帽,肩挑竹筐收破烂的汉子光临剃头店。瞌睡惊醒,笑迎生意,剃头匠热情招呼,客人端坐在理发椅上,草帽一掀,“瘌痢头”,剃头匠神色大变,立马大手一挥,急吼吼甩出了一句扬州腔的上海话:“勿来赛”,汉子扣上草帽,满脸通红,挑着担子悻悻的走了。小店也守住了讲卫生的底线。
小小剃头店不仅是剃头的场所,也是弄堂里人们打发休闲时光的佳地。从厂子里的生产经营到街谈巷议,纵论国事的酣畅淋漓,细说桑事麻事的闲适逍遥。有生活,接地气,成了生活在弄堂中,上海人家离不开的好去处。
如今,一条条弄堂被拆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小剃头店也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剃头匠也不知去了何方。但是,他那周到贴心的服务,成了人们心头永远抹不掉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