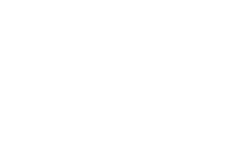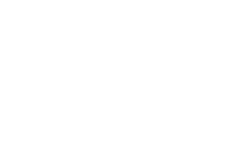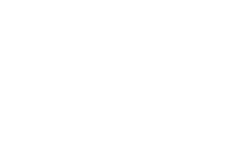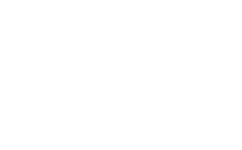去年四月,我趁着“清明”假期,带着想家的那种期盼和喜悦,携妻带女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一路上,满田满野全是乳白色的雾气,像是有层薄纱,把绿色的田野、金灿灿的油菜花、远远近近的村庄都笼罩起来了。
汽车穿过森林、越过河流和平原,来到了我可爱的村庄。我刚下车,雾就把我团团围住,淘气地粘在我的眉毛上,钻进我的鼻孔里,藏在我的袖子上。不一会儿,这乳白色的雾,就化着小小的水珠,洒在我的头发和脸上,轻轻的,爽爽的,潮潮的。
望着眼前的雾气,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也是在这样大雾的早晨,我时常牵着牛来拜谒田埂,牛慢悠悠地从田埂这头踱到那头,又从这条田埂走到那条田埂,它低着头自由自在地忙碌着,如园丁般修剪着田埂上的杂草,它有时吃上几口就停下来反复咀嚼,有时突然昂起头伸着脖子发出一声“哞——”似乎在呼唤着什么东西,在洁白朦胧的轻纱薄绡里,显得飘渺而神秘。我也曾在防洪堤上享受过童年的乐趣,露水打湿了防洪堤,我赤着脚,提着竹篮或背着书包,怀着好奇的童心,蹦蹦跳跳地穿行于湿湿凉凉的河堤之上,让脚底充分感受土堤那柔软极致的舒服。松软的泥浆从我的脚指间蹦出来,产生的那份软软痒痒的感觉直抵心间,让我感受大地的温馨与亲切,感觉人几乎可以忽略的渺小和源源不尽如长江的活力。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在防洪堤上奔跑起来,拼命地奔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我刚拐进家后面的那条小路,就看到老屋前面的那棵高大的酸枣树,现在也只留下淡淡的黑影。远远的,我看到一个妇人挑着一担农产品从我家晒谷场上走过来,我以为是五嫂,正要跟她打招呼,人已走近,我才发觉那是一个陌生的女人。我不禁笑了起来。
正当我失神落魄地自己暗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五嫂的尖叫声“妈!九满回来了!”母亲正在堂屋里切菜,一听说我回来了,她老人家立即从凳子上站起来,我赶紧叫了一声“妈妈!”鼻子一酸,我的眼泪便哗啦啦地流了下来,“九满,我的崽啊!你终于回来了。”母亲哽咽着。
我放好行李,趁着母亲和五嫂为我们一家准备早餐的间隙,打开后门,我想看看朝思暮想的藕池河。雾在藕池河里缓缓地蠕动着,像轻纱,像烟霭,像云彩,河边的竹林、篱笆、草垛时隐时现。几条小船栖息在岸边,点点黄色的船灯在翻腾缭绕的雾气中闪烁迷离。雾气中带着淡淡的草的香味和新翻泥土的味道,带来了几许清爽与清凉。
忽然在白色的云雾中有一个黑点在游动。点虽小,但在白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慢慢地,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哦!是一叶小舟。舟上悬挂红灯,一位渔夫正用竹竿轻轻地拨动着小舟朝这边驶来。那小舟在云雾中穿梭,似有似无,给静谧的大河平添了几分生机。小舟停下了,渔夫摆弄着渔网,开始做撒网准备。
他不急不忙,先用左手把渔网提了一下,然后摊开,再用右手把渔网一层一层地搭在右手腕上。做完这些准备后,渔夫把腰伸直,双眼在水面巡睃,似乎在寻找什么。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渔夫突然发力,他先把身子往后一倾,顺势用将渔网撒出去。
太阳似乎被这撒网声吵醒,从窝里露出半张脸来,也许是感觉该起床了,便像渔夫一样慢慢地把雾收回去。那与清风缠绵的雾,也好似舍不得人间,一步三回头。渐渐的,一个真实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油菜花露出了笑脸,苦楝花排起了队伍;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一会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一会在空中飞来飞去;村庄的上空升起袅袅炊烟,故乡像披上了一层美丽的面纱,更添了神韵,构画出一幅乡村美丽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