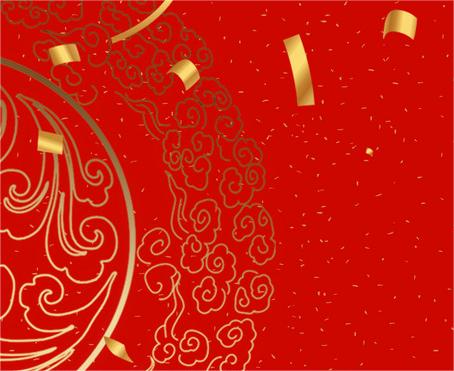中秋节到了,父亲听说我们要回来了,就在家里打苍蝇。苍蝇拍子是父亲自己做的,一块红色橡胶皮,上面穿了许多小孔,用一根长长的竹片夹着。父亲拿着苍蝇拍子在屋里追来追去,他要把屋里的苍蝇全部打完,让我们这些城里人住着习惯。如果这些苍蝇在家里飞来飞去,是多么厌烦啊。
一个黑色的苍蝇飞过来,父亲一举手叭打下去,打死一只苍蝇,父亲就非常有成就感。苍蝇落下来好打,就怕那些苍蝇不落下来在空中飞来飞去,父亲举着苍蝇拍子跟着跑来跑去。父亲老了,每打死一只苍蝇都要停下来大口地喘气。父亲眼睛花了,有时看见一只苍蝇停在地上,用力打下去,那一点黑黑的东西一动不动,凑近一瞅却是一片碎叶子。
那天中午父亲睡觉时,却看到一只大苍蝇在床顶的半空飞来飞去,黑黑的一团,发出嗡嗡的声音,父亲愤怒地爬起来,紧抓着苍蝇拍子,但那只苍蝇却不见了。父亲躺下,刚眯上眼,又听到那只苍蝇嗡嗡的声音。父亲爬起来,拿起拍子就打过去,却没有打着。苍蝇仍在嗡嗡地飞着,父亲瞅准了等它落在墙上,一挥拍子打过去,那只苍蝇打死了,父亲才安然地睡去。
父亲打了两天苍蝇,家里的苍蝇基本上没有了,父亲长舒了一口气。两天后,我们开着车子回来了。
车子一拐上通往故乡的小路,我就从窗户向东边的岗头上望,岗头上是一片浓郁的树林,像一个巨大的葡伏在地面上。过去回来,我总是朝家里的房子处望,每次母亲都笑着站在门前的路上,笑着看我的车子慢慢地驶进。而现在,我的母亲已不在村头,她已安睡在岗头上的树林里。
母亲的去世,伤痛持久地弥漫在我的心里,这种伤痛是一场大雾,久久不能散去,即使太阳出来了,也如苍白的纸片,没有一丝温暖。许多人劝我,要从伤痛中走出来,我也极力劝说自己,不要老是沉浸在这场悲痛中,但母亲的形象总是从一个个熟悉的场景中蹦出来,呈现在我的眼前,只要这些场景在,母亲就在。
车子停在门前,打开车门走下去。天刚下了雨,空气中的凉意深了。父亲的门敞开着,门前空荡荡的。我提着东西一跨进屋,父亲就迎上来主动喊了我一声。要是在过去,父亲会端着架子,等我喊他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变了,父亲的亲切里有着讨好有着欢喜,父亲笑着在屋里转来转去,父亲的牙掉了,一笑嘴里就黑洞洞的。
中午,三个弟媳在厨房里做饭,三弟四弟在打枣,四弟院子里的这棵枣树,还是母亲活着时亲手栽下了,那时是一棵弱弱的小树,不及膝盖高,现在已长成一棵大树了,树上结满了枣子,一会就打了一小筐枣子,用水洗了,一吃脆甜,枣子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但母亲却不在了,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思吧。
菜做好了,一个个往桌子上端。父亲怕一个桌子坐不下,问是否要拼两个桌子,我说挤挤吧,反正都是家里人。大家都挤起来了,桌子上满满都是菜,四周都坐满了人。菜放在桌子上,没有一个苍蝇飞过来,这让父亲很有成就感,父亲说,家里的苍蝇都打完了。
大家都在喝酒了,快乐充满了整个家庭,我想让大家共同举杯敬一下母亲,但想想没有说,怕影响大家的心情。这是母亲离开我们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团圆一直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家风,每逢过年过节,我们就早早地从各地往家赶。以前母亲总是和父亲坐在上席,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喝酒,招呼我们吃菜,那时我们的家庭是多么完整啊,今年,父亲的身旁却空了。
吃过饭,我提议去岗头上母亲的坟墓看看。
地里还是泥泞的,他们都开始换成胶鞋,但田埂上,因为没有人踩来踩去,还不泥泞。田里的稻穗都长出一个个沉甸甸的穗子,但连阴的雨水,有的稻穗上起了黑黑的霉菌,如果天再不晴,这些霉菌就会在稻子中传染下去,就会影响收成。路边的大坝里,水清亮亮的,但坝埂却是一片荒芜的杂草。田地里有一处缺口在哗哗地流水,三弟跑过去蹲下身子,看可有泥鳅,找了一会儿,一个也没有。现在的农田经过整改,与记忆中的农田已不一样了。
走进树林里了,深秋的林子里,铺满了落叶,树头的叶子也稀疏起来。看到母亲的墓了,那一堆小小的土堆,在林子里沉寂着,坟前夏天茂盛的茅草现在也倒伏下去,上次我们来烧灵棚的地方,露出一片黄的泥土,上面还有许多黑色的灰烬。我们站在母亲的坟前,像一棵棵树木,虽然悲伤,但大家都沉默着。我对着母亲的墓说,今年是中秋节,母亲我们来看你了。
小侄子们把带来的橘子、月饼、石榴放到母亲的坟前。二弟开始燃香,风太大,二弟点了半天没有点着,就蹲下身子,用力挡着风,终于把香点燃了,插在母亲的坟前。我抬头看见坟前一棵高高的扬树上,竟垒起一只硕大的喜鹊窝,过去每次来,我都抬头望望天空,望望母亲墓前的这些树,都没有看见,无疑这喜鹊窝是新垒的,我们都惊叹不已。
往回去时,我们的沉重似乎缷下了许多。从高处往村子里看,阴沉的天空下,父亲的房子好像更明亮了些。
傍晚,我们要回城里了,大家都在收拾东西,父亲坐在凳子上,说屋子里还有点花生,让大家带上。过去母亲在时,每次我们走,母亲都想办法让我们带点东西,现在父亲也想这样做,但没有一个人去拿。
我们上车了,父亲站在门口送我们。我叮嘱他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就看到父亲在拭眼睛了,我知道他哭了,他舍不得我们走,他舍不得这快乐就像一股风旋转了一下,就无影无踪。
弟媳安慰说,等我们退休了,我们就都回来住不走了。
父亲低低地说,等不到你们退休了。
但我们还是走了。
晚上,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接了电话,半天没有声音,我问父亲怎么不说话,父亲在电话里哇地哭了,像个儿童。我劝他别哭,父亲抽泣着说,你们刚走,心里有点难过,过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