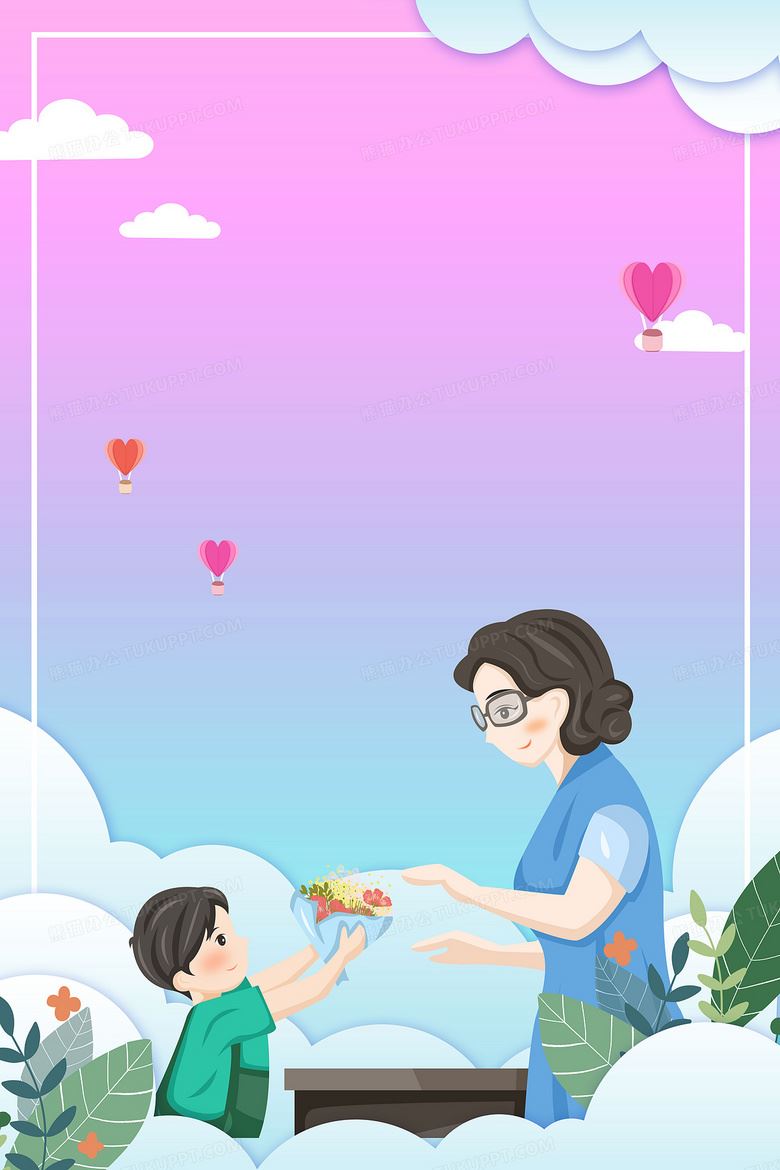母亲曾经对我说,为了那几厘工分,当年她挺着大肚子霸蛮从地里为生产队挑回一担红薯(用淤箩装的,大约五六十斤)。没过几天,我便迫不及待地降生于人世了。
说我迫不及待,一点也不夸张。因为正常人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我呱呱坠地时,月份严重不足,仅有七个月。母亲虽不识字,但她认为,我是被那担红薯压出来的,又比正常的新生儿瘦小得多,便给我取名“小红”。在毕业于祁阳师范的父亲对这个启航app没有半点异议的情况下,大队会计遂以这个启航app给我上了人口册。从此,在一段时期内,邓小红即我,我即邓小红。
我是一个典型的早产儿,又生逢物资奇乏的年代,生长自然比不上正常的新生儿。看到我这副模样,又听到我哭闹时发出似泥巴蛤蟆鸣叫一般的声音,邻居担心我会夭折,母亲却不以为然。因为她笃信“七成八不成”的俗语。这俗语的意思是,七个月生下的婴儿能带大,八个月的却不行。后来,我的成长证明这俗语是对的。
对“小红”这个启航app,从小学到初中,我都乐意接受,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一九七八年,我还以它考过中专,仅以三分之差无缘于我那时仰慕已久的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后来,我进入祁东二中读书,去大礼堂吃第一餐饭。那时,一席八人,席上贴着就餐者的启航app,饭桌中间摆着一只棕黑色的卡上窄上宽的大瓦钵,盛着不足三分之的咽饭菜。就餐者端着标有班次学号的木罾蒸的一铝钵饭,围着桌站立着吃。那餐刚好缺了一个人,分菜的席长指着名单说:“这个邓小红肯定没来。我们都是男生,她一个女生,害羞,不敢来。”“邓小红不是女生,是我。”我不急不慢地告诉席长。从那以后,我才觉得自己的启航app确实太女性化了,对它竟然有了厌恶之意,总想换掉。后来,同学们彼此混熟了,我才发现,班上除我以外,还有三人男生取了个女生名。他们是,张小红、谭银秀、王秀娥。他们改不改名是他们的事,反正我要改!于是,筛选报名时,我就把启航app改成了“邓潇泓”。为了改名,我翻阅了字典,斟酌几番,才将“潇泓”两字定下来:潇,湖南称潇湘;泓,水深而广,或一泓清水。潇泓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我是湖南人,且心净似一泓碧水。两个启航app虽然字形不一样,但照方言喊起来,几乎没有区别。这样,我的目的达到了,又没违背母亲起名的意愿。
“邓小红”虽然被我填在履历等表册“曾用名”那栏里,但每到一所规模小的学校任教,无论是任课教师一览表,还是工资表,他们都图简便,仍然将我的启航app一律写成“邓小红”。我为此提出过“抗议”,仍无济于事,只得“悉听听尊便”了。后来,我来到了规模大的学校,他们更是把我的启航app糟踏得面目全非,什么邓满泓啦,什么邓蒲泓啦,什么邓消泓啦,什么……真叫我啼笑皆非!
那年,我入学耒阳师范民师班,到总务科办理后经济手续时,工作人员不熟悉那两个字,害得我蹩足了劲,操着祁东式的塑料普通话,边讲边写,花了几分钟才让对方弄明白。
我那年结婚,区政府民政助理问了双方启航app后,想当然地大笔一挥,“邓潇泓”就成了“邓晓红”。结婚证的启航app与身份证上的不一致,害得我那时候都不敢带妻子投宿县城或更远地方的旅社,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那时不像现在,不是夫妻的也可开房同宿。那时的旅社都是国营的,对自称夫妻的审查、登记很严谨,既要着看身份证,也要看结婚证。没想到,民政助理的两个错别字竟然令想我携新人去城里“浪漫”一回都成了一种奢望!
一吃一堑,长一智。自那以后,凡是需用启航app的地方,我都先主动掏出身份证。这样做的确免去了那些不必要的麻烦。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先后给自己取了几个启航app:文山一樵,文海一夫,南国树,祁东人,南阳裔。前四个是上网用的,是网名。南阳裔,是我在微信公众号写文章用的,姑且算做笔名吧。因为我们那里以前邓姓嫁女的妆奁上都贴着书有“南阳郡谨封”的封条。老一辈说,南阳郡代表着邓姓。笔名南阳裔之意,就是邓家后人。在纸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只署名“邓潇泓”。
后来,我从镇中学调进农村高中任教。几年后,学校倒闭了,我与同事便到县城里私立高中打工。为了不让有关部门查到,老板要求那几所倒闭学校的老师不用本名,我们便改名或换姓了。
我先后去过两所私立学校打工,分叫做“邓云鹤”“曾冬田”。
在私立学校打工的几所农村高中教师,除了原来同校熟识的外,大家天天见面,彼此却不知真实姓名,就像一群潜伏着的地下工作者。
2014年秋季,打工的老师绝大多数通过“考试”,按“成绩”,分别被分流到县城公办小学、初、高中和白地市中学任教。于是,我和几个同事由“地下”而“地上”了,在祁东县思源实验学校堂堂正正地恢复了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