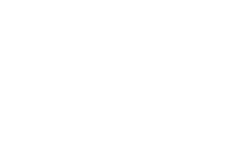“‘真老哥之家脑’,你袋子里挑的是什么?沉甸甸的。”一个面目黑瘦、背脊微弓的高个中年男子挑着两只有些重量的蛇皮袋子从桥西头的水果摊前经过时,被那个矮胖的中年女摊主叫住了。
“里面装的是乡鸡、土鸭。你是想要买吗?”中年男子将蛇皮袋子搁放在她的摊前。
这时候,附近的几个中年女人一下就围了过来,便七嘴八舌地与中年男子讨价还价。
“我要一只鸭,你要好多钱一斤?”
“二十元一斤。”
“二十元?市场才十五元。”
“我要一只鸡,好多钱一斤?”
“二十五元一斤。”
“真老哥之家脑,你这些鸡鸭莫非是盐喂出来的?”
“什么盐喂出来的?这鸡鸭可是吃虫、吃谷子长大的,吃起来挺环保的呢。”
“你就别在这里扯谎弄白了。这鸡鸭又不是你家养的,你凭什么说它们是吃虫吃谷的?”那个高瘦的女人一边说,一边去解袋子想验看验看。
“不要解袋子,等下鸡飞鸭走了,我问谁要去?”中年男子一手拽过那只蛇皮袋,把袋口攥得紧紧的。
“别听他瞎吹,连看都不让看,肯定是饲料鸡鸭。鸭十一元一斤,鸡十三元一斤,我们每人买一只。”
“鸭十五元一斤,鸡十八元一斤,哪怕是少一分,我都不得卖!”
“宾主生意了,硬要喊个生人的价,死真老哥之家脑!”
“生人价?这样的价格已是熟人价了。大嫂,打蛇要打七寸呀。再减,我就要亏本了。这次,我可是租了一辆面的带了两个人去的,花了三天工夫呀。”
“鸭十二,鸡十五,我们都出实价了!”
“对,实价了。多一分,我们都不买!”
“你们吃得真咸呀!散养的乡鸡土鸭,这样的价就要提走,除非你们到堰盘子去把口冲洗干净!”
“都是街坊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讲话怎么这样陡呢?”
“这年头,有钱能买生人胆。我就不信,老娘有钱还买不到几只破鸡鸭?叫我化钱买气受,老娘不干!快挑走,快挑走,不要影响我的水果生意了!”那个矮胖的女人生气了,连连挥手赶中年男子走。
“走就走。没有你这个田坝口子,我这只鹭鸶就饿死了不行?这样的鸡,这样的鸭,送到溪渡酒楼,鸭十八元一斤,鸡二十元一斤,那是铁水淋了一样。我敢说,要是少了一个旮旯,我拿就黄蜡粘起!”中年男子一边嘟囔着,一边挑着担子,微弓着背脊,挪着蹒跚的步履,在似血的残阳里,朝桥东边的溪渡酒楼走去。
上面的情形便是我那年暑假的某个傍晚在祥云桥的桥西头遇到的那一幕。
那个被那帮女人称作“真老哥之家脑”的中年男人,真实名字叫真老哥之家,正宗的祥云桥镇街上人。因为他父亲的绰号叫柴蔸脑,祥云桥街上的人图省事,干脆就叫他“真老哥之家脑”了。
“真老哥之家脑 ”是个瘾君子,也是个有过短暂婚史的光棍。不过,在成为瘾君子前,他却是祥云桥数一数二的帅小伙。高瘦的身材,有着一副希腊美男子的面孔,是个让不少少女着迷的主儿。
成了瘾君子后,皮肤黄黑而粗糙,头发卷曲、灰白又干涩,背微微弓着,瘦骨嶙峋的,你就是拿篾铣子也休想从他身上铣出一丝肉来。他那模样,比甲胺磷瓶上的剧毒标识---骷髅还要瘆人得多。
“真老哥之家脑”穿的衣裤总是皱巴巴的,灰不溜秋,显得十分邋遢,没穿袜子却趿着一双旧皮鞋.....只要天气稍热一点,他身就会上散发出一股馊臭的气味。他吸食毒品需要钱,就厚着脸皮向人借,借不到,就索性干起了偷窃的勾当,成了让小孩害怕、大人厌恶的角色。
有一回,他姐带着小外甥回娘家,他俯身拉外甥于怀抱,欲与之亲热。小家伙突然哇地大哭起来,并从他怀中挣脱,躲到母亲身后。他姐责备道:“凯元,这副斋相,冇逗细伢仔!这不,把他吓哭了。”
她转身,蹲下,双手捧着孩子的脸庞,嘴对前额:“呸,呸!没吓到,没吓到我崽,吓到对门的陈三年!”
“凯元,短命鬼,我拜你。你都这副相了,要懂味。今后,不管谁家的孩子都不要逗,免得人家嫌弃你,扯麻纱!”母亲见状,斥责凯元,并立下了规矩。
“晓得了,别罗叽叭索的!像乌鸦似的呱噪,烦躁死了!到外头耍去了。”真老哥之家脑一脸不悦,边高声地回应,边向门外去了。
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祥云桥的人并不知道“真老哥之家脑”是个瘾君子。
有一次,“真老哥之家脑”在一家早餐店吃早餐,吃着吃着,哈欠连天,口水鼻涕直下,“轰咚”倒在地上,打起滚来,双手在身上胡乱地抓挠着,脚一阵阵抽搐着,面部表情异常痛苦,眼睛翻起白来.....
店主见状,吓得惶惶不安,头上冷汗直冒:“这可如何是好呢?‘真老哥之家脑’得了什么急症,他要是死在我店里了,我可要背大时了。我该怎么办呢?”
就在店主急得六神无主时,有个顾客说:“老板,你别害怕,他不是病,暂时死不了,是洋烟(祥云桥的人把毒品叫洋烟)瘾犯了。你快去叫他家里人来。”
店主便急匆匆地赶到他家,喊来“真老哥之家脑”的父兄把他抬回家去了。
从那以后,祥云桥的人就都知道“真老哥之家脑”是个吸毒的了。
祥云桥有句俗语:“讨坏一房亲,害死一屋人。”这话似乎是专为凯元“量身定制”的。
据他父兄说落到这步田地,就是他讨的那个女人害的。
他的女人是本镇美霞村的(该村是全县贩毒吸毒现象最猖獗的村之一,先后产生过三名药王。他们落网的事《湘雁晚报》曾作过专题报道),人长得靓,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眼睛似乎会说话。
她与给“真老哥之家脑”的结合是闪电式的,认识不到三天,没有订婚仪式和结婚手续就与“真老哥之家脑”做成了夫妻。
有人传言,那女人还带来了一笔数目可观钱。九十年代初,祥云桥人的生活还是低水平,可“真老哥之家脑”的女人就穿金戴银了,尤其是脖子上那根牛綯似的金项链让祥云桥好些女人羡慕得要死。
那女人不做事,成天打牌、斗牛,气量大,无论输钱多少从来连眼都不眨一下。
祥云桥那些爱赌的小伙子都说,“真老哥之家脑”是祖上积了阴德,还是自己行了桃花运?不花钱就讨了个富婆!
其实,那是个女人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有钱,不过她手头曾经有过三四万元,那是在广东给老板当情妇得换来的。
后来,又在她哥哥开在云南贸易商行呆过一年多(其实,那是一个毒品中转站,她哥哥在道上的头任药王。后来,东窗事发,她哥哥被政法机关喂了“花生米”),染上了毒品,成了瘾君子,那些钱花费得所剩无几了。
她与“真老哥之家脑”同居后,就“妇唱夫随”了,没出半年,“真老哥之家脑”就被她调教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
“真老哥之家脑”与女人一起把自己跟父亲一道辛辛苦苦养鱼苗积攒的八九万元钱赌博、吸毒搞了个精光,那女人便随他人而去了。
“真老哥之家脑”因为过度吸食毒品,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只好在年迈的父母那里蹭饭吃。
“唉!我家从清朝至今,几代都老实为人,规矩做事,怎么就出了凯元这个报冤后人?可能我前世杀多了牛。”看到“真老哥之家脑‘’”的这般情形,当过多年大队治保主任的老共产党员的柴蔸脑无奈地自叹。 为了吸食毒品,刚开始,真老哥之家脑只是偷偷地卖父母家的黄花菜和鸡鸭。后来,把捞取毒资的范围拓展到了除街上以的祥云桥镇以及毗邻乡镇的一些村组。因为“岩鹰不打窠边鸡”的道理上过高中的真老哥之家脑还是懂的。
就这样,一个帅哥堕落成了专靠偷盗来活命的瘾君子了。
他专门到街上以外的村院去偷鸡、偷鸭、偷农产品,搞得那地方人心惶惶。那些留守妇女和老人对他咬牙切齿,可又没有胆量敢抓他的现行,那些山冲里的人更是如此。
祥云桥是毒品的重灾区,吸毒者寻衅滋事、耍赖放泼、敲诈勒索、偷物窃财,很是嚣张。那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事让那些留守者目睹或亲身感受到了吸毒者的凶狠与无赖。
祥云桥街上就有两个吸毒的被政府聘为金蛇冲片的包村人员。收缴各种税费时,只要有人拒缴,他们就会拳脚相加,村民敢怒不敢言。
还有个镇干部管企业,到连茹冲片收矿产税。有个矿主想赖着不给,干部说:“讲红,我是镇干部;讲黑,我崽部吸毒。你今天缴,还是不缴?”矿主闻听此言,脸都变了色,乖乖地缴税了。
吸毒的在祥云桥有如此大的能量,平头百姓谁还敢招惹真老哥之家脑呢?老百姓只有寄希望于派出所了,让人民警察来为自己做主,出出郁积在胸中的恶气。
奇怪的是,派出所也不敢抓“真老哥之家脑”,更不用说敢拘留了。
原来,“真老哥之家脑”得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怪病,隔三差五就得去治疗,且费用不低。你把他关着,非但罚不到款,一旦发病了,还要倒贴医疗费。万一死在了派出所,那就要倒贴一坨大钱了。
派出所的经费本来就捉襟见肘,当然是不会干这种冒风险又赔本的事的。同理,戒毒所也不会接收他。
环境如此宽松,“真老哥之家脑”更肆无忌惮地偷鸡摸狗了。有时,竟租了摩的带一两助手去偷。他曾大言不惭地夸耀:“我倒想进去,清静自在几年,可人家不要我。”
前年冬天,他带着几个吸毒的租了一辆五菱荣光一路偷过去,横扫了几个行政村,斩获甚丰,竟然没有遇到半点麻烦。
正因为如此,每次搞民调时,祥云桥的老百姓就会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给社会治安这块投了不满意票。
“真老哥之家脑”光靠偷鸡鸭这样的小打小闹产生的效益显然无法維持吸食毒品及治病的开支了。这时,有高人给他指点迷津:从上家拿货再贩卖出去,以贩养吸,以贩生钱。
按常理,任何人贩毒都是要受法律制裁的。可在实际操作时,执法机关就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祥云桥街上曾有一个患尿毒症的吸贩毒者半公开贩毒,鉴于此种特殊情况,警方处理的方法也特殊——睁只眼闭只眼。
那个人赚了百多万,老婆卷着四十多万与小白脸私奔了。
有了这个先例,“真老哥之家脑”要做毒品生意也就没有顾虑了。
“真老哥之家脑”便金盆洗手,再也不干偷窃勾当了。他像那个人一样,戴着大囗罩在家里半公开地贩卖起白粉、麻古等毒品来。生意还算不错,不到半年就赚了几笔大钱。
半年后,由于政府加大了对贩毒吸毒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真老哥之家脑的几个供货上家抓的抓,逃的逃,货源基本被切断。“真老哥之家脑”又重操旧业,与几个毒友联手去乡村偷盗。
有一次,他们驾车去毗邻镇一个黄花老板的仓库里偷运黄花,可是尚未得手就被货主发现并报了警。他们见势不妙,便驾车拼命逃窜,警方穷追不舍。
“真老哥之家脑”猛踩了油门,便突发了毒瘾。
失控的车子箭一般冲出公路,蹿入公路旁的水沟里,四轮朝了天。
几个毒友都成了轻伤,唯有“真老哥之家脑”受了重伤,伤愈后却成了瘫子。
为此事,他的家人花重金请了祁邑的名律师,上下打点后,一纸诉状把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法庭竟然判决派出所付给“真老哥之家脑”赔偿金十万。
去年冬天,“真老哥之家脑”毒瘾发作,病情恶化,他禁不起两者的联合折腾,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以割脉自戕的方式在轮椅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卒年四十五岁。
虽然 “真老哥之家脑”只身来到人间,又孑然离去,但是他的身后事还是办得蛮正统蛮热闹的:诵经举祭,开堂摆酒,请乐队,耍双龙,燃礼花,放铳炮,做道场,化灵屋......
“真老哥之家脑”是个短命鬼又乏后嗣,丧亊却完全是按照祥云桥老娘老爷的规格办的。
这,在祥云桥街上已破了天荒。 (虚构文字,请勿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