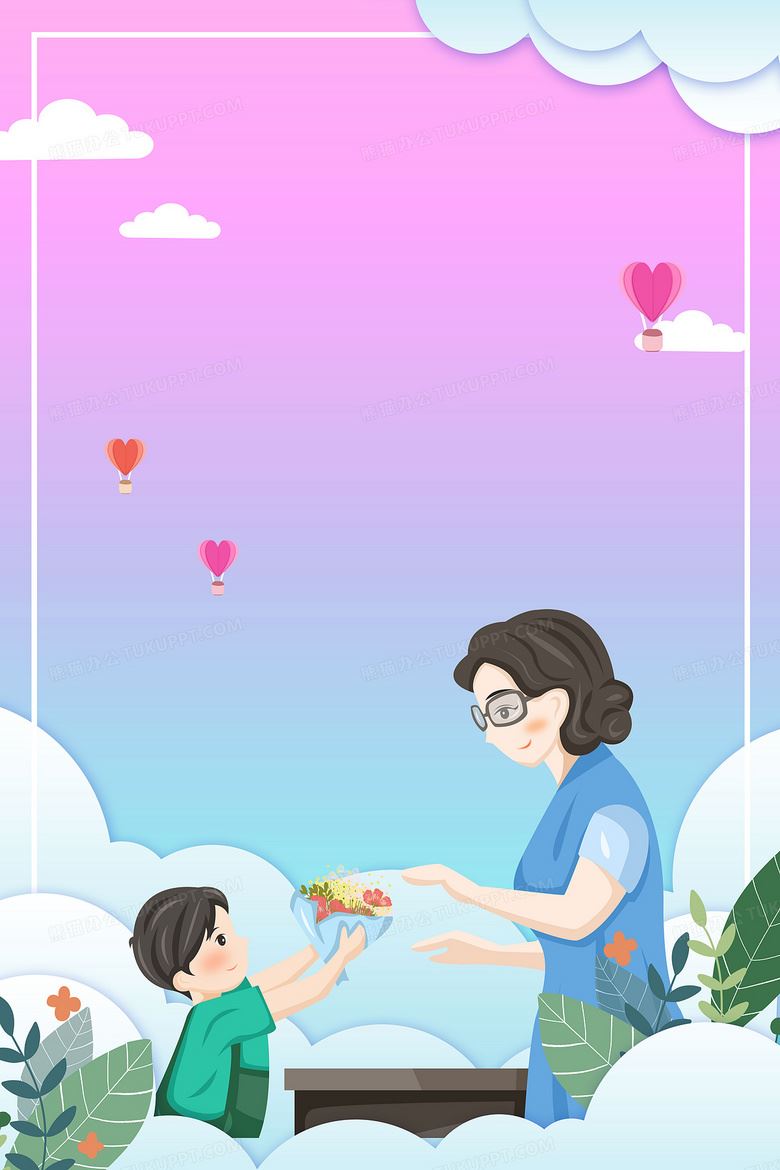在乡村,蝉,是季节的歌手。整个夏天,只要有树,就会有蝉。只要有蝉,就能听到蝉在歌唱。
清晨,一只蝉率先发出单音的独唱,像号子般,紧接着就有无数只蝉在四面八方响应,都亮开嗓门,跟着唱起来。于是,“知!知!知……”声此起彼伏,构成一曲恢宏、响亮的大合唱,如交响乐般丝竹管弦一齐鸣响,不绝于耳。
说起蝉鸣,我又想着幽居于泥土深处的蝉。
一只蝉,独自生活在泥土里,两年,三年,抑或五年八年,北美洲甚至有长达十七年的蝉。它们在喑黑的环境里,默默地吸吮植物根部的汁液,默默地成长,黙默地打造向上向光明的生命通道。没有光,没有声音。只有黑暗,只有泥土。
不知是哪一天,也不知是哪一年,在生物钟的催促和外部环境的刺激下,蝉意识到出土的时机到了,便从容不迫地从幽居的土室里钻出来。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树、植物茎干、篱笆或电线杆上,爬得高高的,找到合适的位置,停下来。棕黄透明的蝉虫开始蜕变,首先从背后裂开一道缝,之后肉身从缝隙间闪出来,换上漂亮的衣服,露出可与鸟类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生命真的是很奇妙的存在。
从此,蝉尽力、尽情、尽心的歌唱,狂热、虔诚,振聋发聩,不绝于耳。
每一只蝉都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歌者,它用一生的歌唱来展示生命的存在。这激越的声音是生命苦涩深长的啸歌,是对光明的崇拜,是生命长期被压抑选择的释放和迸发,是展示自己生命存在价值的浑厚的争鸣,是大自然的天籁。
安静的时候,让我感觉温暖的蝉像是一个个淡雅的少年,它们趴在树枝上想着自己的心事。瓦蓝瓦蓝的天空之下,在干净清新的空气里成熟,在明亮充足的月光下甜蜜恋爱。在一场大地上最张扬最浪漫的爱情大戏落幕之后,雄蝉率先走到生命的尽头,从枝头坠落,缄默无声地回归大地。雌蝉则要完成其终极使命,将卵产到精心挑选的树枝里,之后才会追随亡夫而去。
蝉,在幽暗的地底困守了那么久,可是,当蝉用尽整个生命的力量爬出泥土与腐叶,在露水与阳光里放纵啸歌。只有一季。只有一季啊!那么短!却是那么的努力拼搏!
很久以前,父亲手指蝉对我说:“做人要学蝉,实诚,勤快,知足。唯有实诚,方得信任;唯有勤快,才有收获;唯有知足,终会长乐。要珍惜好时光,做有意义的事情。”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必须努力,千万别指望走捷径。
从那时起,我发奋读书,学习不停地变奏着紧张忙碌的篇章,岁月的喜怒哀乐奏响起我生命长河中澎湃的华唱。年复一年,我与那些餐风饮露、择高而栖的蝉一起追梦,一起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生命之歌。在和蝉相守的日子里,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东西——自强的力量,自信的力量,伴我坚定地前行。
我每天都重复着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内容,在书山题海中穿梭,在牢狱般的“梦工厂”里挣扎,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纷纷钻进我的大脑,坐标系更是带着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在我的脑海里旋转,让我昏头转向,把我这个急于跳出农门的少年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为大量需要记忆的政治、生物知识废寝忘餐,我为数学、物理、化学习题夜以继日,更为English的单词和语法夜不能寐,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像蝉一样,用并不充盈的体力却十分顽强的意志与睡魔、失眠进行着激烈地交锋,每天都承受巨大的压力,却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放松!
那年夏天,蝉从黑暗的洞穴里爬出来,向高处走,向远方走,飞向那一片纯净湛蓝的天空;我也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圆了我的大学梦。
随后,我告别了亲人和朋友,也告别了故乡的蝉,走过村头,跨过那条伴我成长的藕池河,在省城长沙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
四年之后,我带着大学生活积累的学富南下广州……
工作上,没说的,像蝉一样,实诚,勤快,知足。
我每天雄赳赳、气昂昂地出门,挤着公共汽车上班下班,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灵魂在喧嚣的尘世间奔波忙碌。
一晃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了,我混的虽然不尽人意,但我知道这份工作凝聚着自己的心血,承载着父亲的希望。我想,如果没有像蝉那样的努力和坚持,说什么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越来越确信,我的血液里住着蝉的基因,我性格成分中的偏激、刚性、爆发力都源于蝉。是蝉,在意识、秉性上给了我某种冷峻、坚硬和笔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