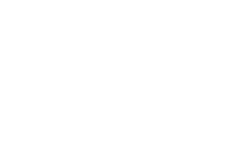在我家的家神正中,端正地摆放着一张镶框的照片,照片是请人用碳笔画的,已二十多年了。我成家后有三次搬家,最后一次临时住在用花亮纸搭的工棚里,那夜下起大雨,我醒来时被子已湿透,我裹起被子、枕头和枕头底下的碳笔画的照片,逃亡似地跑到租赁的房屋外,唤了20分钟,原本在咳嗽的主人静下来,但迟迟不开门,不得已,我又返回工棚,找了几个塑料口袋包好这张相片,一直坐到天亮。
这张照片上画的是我奶奶,她包着青布帕子,穿着青色的操襟衣服,脸颊高高地鼓着,眼神露着能洞察一切的沧桑。相片下是一张大理石饭桌。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奶奶的对面,仰头细嚼着饭食,就可以见着奶奶在动——她的灵魂,在我思念的空间里游丝一样浮着。
奶奶是上吊死的。凡上吊的人,都喜欢选择了白绫,高高地挂在楼楅上,用一种极端的死亡方式,解决长久积压的愤懑或忧郁。但奶奶自杀的工具,简单得很,是一根从牛鼻子上割下的牛绳。她断气后,我闻信赶回家,能嗅到么叔家满屋里都是牛鼻子上那种怪怪的膻味。
奶奶断气的一瞬间,满寨的人像疯子一样跑到幺叔家,么叔与么娘气定神闲地坐着,怔怔地看着套在牛绳上的奶奶,奶奶还像孩童坐在秋千上一样晃荡。我的堂哥放下奶奶,用力捏开奶奶的嘴,将她吐出的紫黑舌头塞了进去。
奶奶,在她若无其事的小儿子面前,去了。没有经过痛苦的病魔,只留着谜一样的临死结局,让人去痛苦地怀想。
在为奶奶操办后事的时候,我与么叔一样,穿着长孝衣,尽着那份虚伪的孝道,听着总管与道士不尽人情的吼叫,我忍受着,待远离了总管与道士,我就直愣愣地瞪着么叔看,我的目光里一定有毒。
我的奶奶,在选择上吊的前几个月,曾经选择了跳水的死亡方式。我母亲听到奶奶在水井里喊救命,忙扛了楼梯去救她,其他的人听到“救命”声,也一路小跑了来,见奶奶稳稳当当地坐在水井里一块突出的石头上,她的身上没有一滴水,这事让邻居们明白,我的奶奶,虽到了八十七岁高龄,仍留恋着尘世里的笑声与阳光的。
自我记事起,奶奶就一直在幺叔家过活。我的有血缘关系的上辈中,有大伯、父亲和么叔。大伯是另一个奶奶生下的,却是我的奶奶拉扯长大。在一次争吵中,大伯提到了分家的事,说他在分家时只分了一口铁锅和一对水桶,对于赡养老人的事,要一丝纱,也没有,奶奶流着泪提起板凳向大伯砸去。后来的几十年里,大伯真正地说话算数,兑现了自己不赡养老人的诺言。但每次料理老人的后事,他却跳得最凶,似乎连炸在地上的爆竹壳也要捧进家里才安逸。
我的父辈们全部成家后,赡养奶奶与爷爷的责任,由父亲与么叔承担起来。
在爷爷与奶奶分家后,奶奶向我诉说了一件揪心的事,说我其实还有一个叫二伯的,只不过二伯在抱着么叔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么叔掉在了地下,当时奶奶正在砍猪菜,心一急,翻起猪菜板摔了过去,二伯当时鼻孔只流了几滴血,不几天却死了。奶奶说起这事,脸上全是悔恨的泪水。不久,我知道了二伯的坟在一个迎风的丫口上,那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小的土堆,里面就是二伯,看来,么叔的命里,竟有两条命的影子,是以,么叔就格外地受到奶奶的疼爱,以至于能读到六年级。在我的记忆中,读三年级的父亲能教我如何作文,虽然有时跑了题,但那份责任却没有跑题。而我的大哥(么叔的儿子),在我参加工作后的六七年里,仍没有考上一所学校。细想起来,父辈的教育有时还真的有些让人思索的成分。
记得有一次,大哥回家要学费,么叔很是不耐,顺手拿起斧头要砍向儿子。大哥急忙提起菜刀爬上楼梯,父子俩横眉对峙,奶奶颤巍巍地隔在他们中间,泪眼婆娑地劝说,浑忘了他们手里那锋利的武器。这事像一个肉眼看不见的音符,它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么叔用来对付儿子的手段,会不会用来对付奶奶呢?
么叔家住在我家坎上,相隔也仅几十米。爷爷与我们住在一起,他的嗓音很洪亮,天都被震得当当响,爷爷的每一句说词,在两个不同的屋里,奶奶都能听见,她就站在幺叔的门口看着爷爷笑。但凡父辈们去干活,爷爷就坐在门口的草鞋凳上,轻声地叫奶奶来抠背,有一次,我分明看见爷爷笑着去抚摸奶奶的乳房,那时他们还算年轻,而更年轻的父亲与幺叔,为何要生生拆散这一对年轻的老夫妻呢?
父亲是全寨里公认最会事、最孝顺的人,但他却像是一朵礼花,只把旺盛的生命展现在夜空里几秒钟,就毫无牵挂地潇洒去了,徒留爷爷奶奶呼天抢地的哭声。两月之后,爷爷去给父亲做伴,那时他已八十六岁了。
接连的重创,让奶奶一下子苍老了不少,奶奶开始与么叔闹起了矛盾,她要另起炉灶煮自己的饭,也用么叔种的粮食喂起了鸡,么叔就用敌敌畏拌了粮食撒在奶奶的鸡笼里,高大的奶奶哭着去撕更高大的幺叔的衣服,被么叔摁在灶台下半天起不来。奶奶沉默了半个月,自己带上锄头上了山,开始种地。
自耕自种的奶奶养了20来只鸡,鸡每天都要轻轻松松下十来个蛋,奶奶就用荞壳垫底,把蛋整整齐齐地排放在竹兜里。每逢妈妈思念父亲和爷爷,坐在门口哭泣的时候,奶奶就拴上围腰,再把围腰翻转来,装上鸡蛋,给我妈送去,那时我的妈妈,安葬了丈夫与公公两位老人,家境穷得快要舔灰了。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奶奶与么叔分家另过,不外乎是想接济一下被生活逼向绝路的我的妈妈。而我在70里外的异乡,可以利用周末,徒步走回家里,从高坎子上挑几挑水,倒在那半月型的水缸里,让妈妈备用。奶奶一见我回家,老远就笑着叫我,再捞起围腰擦擦眼角。有一次我带上未婚妻回到家里,外出干活的奶奶回来,躲在那月样的水缸旁,透过扩来挡风的扬耳笆(竹子编成的块状物)偷偷地看。我看到奶奶的身影,急忙跑出来,吊着她的膀子仰着脸笑。奶奶问吃饭没有,我说刚到家,她就转身到么叔家去了,一小会,她用围腰兜了几个鸡蛋。未婚妻到屋外看风景去了。我赶忙在灶膛里架起柴火,奶奶就磕破鸡蛋,到处找油,可灶边的坛坛罐罐全空得好看极了,奶奶嘴巴一撇,想哭,但忍住了,急忙回到自己的家,舀来了半碗油。
我家的灶用石头垒成,安着两口大锅,灶的缝隙用黄泥巴抹实了,火一燃起来,却从锅口冒了些青烟,烟满屋乱窜,奶奶就用手扇着那胡乱窜动的烟子,吭吭地咳,但我却听到油在锅里嘶嘶地炸响。待鸡蛋煎得很薄很黄的时候,一只中指长的长脚蜈蚣在灶膛里受了热,从灶缝里钻出来,毫不客气地爬向锅里,奶奶握紧用锅铲把锅凿得嗒嗒地响,但最终没有压住那可恶的蜈蚣。蜈蚣翻起肚子,在那让人馋涎欲滴的鸡蛋香味中,死了。奶奶急忙叫我关好厨房门,她顾不得锅里的汤有多烫,忙用袖口粘起那只讨厌的蜈蚣。“雷公虫有毒,不能吃了。”我对奶奶说。奶奶紧张地看着厨房门外,将我拖过来压在她怀里,警告似的说:“不要说出去,我先尝。”奶奶舀起半碗汤,胡乱吹了几口,忍着烫喝了下去,我几次用手去拖,都被她狠劲将我的手拍得垂下。
这一顿饭吃得好是难过,如果脖子也能够哭泣,我想,我的脖子里一定早就溢满了了泪水。
这事过后近一年,奶奶上吊死了,当乡邻们把她抬上了山,我回家收拾奶奶的旧衣旧被准备火化,却看到奶奶的枕头底下压着的,不是钱,而是一条长长的老蛇蜕掉的蛇皮。或许一年,或许更长的时间,我奶奶床上的衣物,么叔么娘及他们的那八九个子女,都已经忘记替奶奶翻洗一次罢?
奶奶在她最疼爱的儿子的房里,在一个叫“遗忘”的词里,去了。她的坟与一座不知名的老坟一起并排着。
为了不让奶奶的坟与那所坟混淆,我找来一块红色的石头,在没有碑的坟的前端,恭谨地画了一个“十”字。
(编辑: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