瑾的诗歌孤独又美丽,我从不掩饰对它们的偏爱。“嗨,你感觉怎么样?我刚在路上写的。”她喜欢时不时抛一首新作过来,并询问我的意见;“孤独,浅浅的,似乎身处于无边的旷野;可是一点也不悲凉,因为头顶有大片的星河,清醒、美丽,有某种温热的力量;涌动、翻滚,悄无声息间传输着一些火光般的东西。”我大段大段发表着读后感,总还觉得意犹未尽。就好像我笔下的,那个所谓的“火光”般的东西,已经在我的心里彻底燃起来了。她嗤嗤嗤地蹦过来一连串又哭又笑的表情。
“一个人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简直太美妙了。”说到星河,我俩自然地扯到看星星上来。“对嘛,夏风凉凉的,舒服死了。”我的记忆,瞬间回到了秦岭南麓那面背风的山坡上。那是七月的夜晚,我将帐篷的外账整个扯下来丢在一边,夜色顺着内帐的纱网从四面八方挤进来;我躺在睡袋上,哼着歌,翘着腿,眼盯盯看着易游娱乐调皮的小家伙。它们挂在离我很近很近的天幕上,似乎只要一伸手,就能摘下来一颗两颗。
那是我疯狂迷恋户外徒步的一段时间。整整五年的时间里,只要能请到假,都会一头钻进山里去。少则一天,多则四五天,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从一条古道寻到另一条古道。我不喜欢走走停停三步两歇的观光团,所以只和少数几个趣味相投的“自虐党”一起行动。一口气走两三个小时,休息时就集体躺在草坡上或树荫下。当身体经过大强度的运动后,突然松懈下来的舒服感,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清风荡着草木和山花的清香,一浪一浪往鼻子里钻;叫不上名字的鸟雀停在不远处的树枝上,歪着头瞅着横躺竖卧的人,时不时啾啾叫上几声。在那样极度舒服和困乏的环境下,我会几分钟之内就沉沉睡去,香极了。
时间充裕,不需要赶路的时候,我喜欢长时间躺在某处地方,不说话,不动弹。初春冰刚化的河边巨石上;盛夏花正开的向阳草甸上;深秋里一踩就吱吱作响的落叶林里;即便是冬季的白雪皑皑,我也要兴冲冲跑过去,跳着笑着,跌进厚厚的落雪里。
山林并不寂静,我闭着眼也能看到各种的喧闹和故事;那是完全不同于人类活动的另一种,让人无比舒适和享受的喧闹,它们和谐、积极、彼此照拂,它们有着完整的自由和世界。那样的时刻,我是它们其中的一份子。我会低声哼着些找不到调的小曲儿;也会“啾啾”“咕咕”应和着某只正在兴头上的鸟雀,并想当然地给它定个正在恋爱的痴情角色;我会躺着躺着突然就想起某件特别有趣的事,紧接而来的是一串嗤嗤的傻笑。没人在意我那神经质的傻笑,他们压根管不着。
正在扭动身姿的旱芦苇能管得着;起劲儿拍手掌的栗子树能管得着;草丛里悠闲啃着嫩芯的黑壳虫子也能管得着,可它们多精明,才懒得理会旁人的事情。我有些愚笨,跟精明一点不沾边,可从小到大都心思简单,就喜欢专注自己的小世界,做着些旁人眼里“毫无易游娱乐”的事情。
说起“易游娱乐”,我和瑾双双愤青起来,“要什么易游娱乐?什么易游娱乐不易游娱乐?真是好笑。”“啥都要找出个易游娱乐,无聊得要死。”好像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必须要成家过日子;好像一篇文字就非得映射出什么深刻的道理来。相较于动辄你死我活的爱情故事,还有跌宕起伏高潮不断的卖座文字,我更喜欢清淡和真实。鸡零狗碎,却透着丝丝温情的生活片段;秋水般宁静,却也淡而有味的平常爱情。它们没有完美,也不会时刻新鲜,可恰恰才是生活最真的样子。
直到现在,我还是常做一些看似毫无易游娱乐的事情。一个人顺着河沿走好几里,一棵一棵点垂柳和白杨的数;在新春路尽头的草坪边坐一个下午,等那只叫来福的哈士奇;和隔壁小区的退休老奶奶相约周六下午去喂流浪猫,她橘黄色的挎包里有猫粮,有一本家庭相册,还有为我准备的甜点。我俩给很多猫咪都起了名字“小老虎”“黄丫”“白手套”,时间一长,小家伙们一叫一个灵。叫到名字的便会跑过来蹭蹭我们的裤脚,接着顺势躺下肚皮朝上一翻,等着我给它们挠痒痒,等着从老奶奶的手心里吃东西。“孩子,你快看,‘小老虎’又胖啦。”奶奶一直都这样叫我。“奶奶,你是不知道,‘小老虎’完全就是个花心大萝卜,来者不拒嘛,成天屁股后面跟好几个妃子。人家妻妾成群,日子滋润着呢。”我和奶奶走一会儿,唤几声,给隐蔽的墙角和树下放一把猫粮,慢慢走着,聊着,笑着。
“嗨,我们要不要来玩歌曲接龙?”瑾的信息又来了。“好嘛,就接龙王菲和张国荣的,来来来。‘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我张口就来;“我在你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我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不管夜深,不惧——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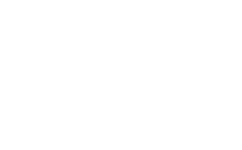





![【系列连载】★缘梦致语天地情[散文随笔组章之一篇]](/d/file/zheli/renshengganwu/2023-05-30/0e8b3c998bcb43b9204eb5e6b7d3a53d.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