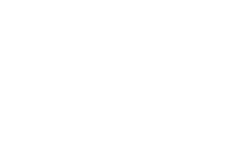程锦如,70后时尚美女作家,马越关山,文章几乎踏遍长城内外各大晚报副刊。新近在《锦都晚报》“物质女人”栏目上开设“锦年如花”专栏。文字青春时尚,娇艳玲珑,袅袅如有巫气,自是揽下一批粉丝追捧。
人都好贪心啊,当初拾笔才出茅庐时,唯愿文字赚得小名之余,还能换得一盒两盒的胭脂口红,捎带着裙子若干。后来不甘了,竟还要按揭买下一栋别墅,日日拼命写稿还贷。后面还跟着一宏愿,将来债清后,还要出国旅游,写上一本“欧游杂记”之类。
但是,久在江湖行走,难免撞见80后乃至90后的文字在版面上,飞扬跋扈与自己擦身而过,心里常常惶恐,感叹自己已不年轻,怕自己的文字相形之下也年老色衰,如死鱼浮于水面,再无人光顾。心态很重要,保持年轻的心态。于是,程不论春秋与寒冬,总是穿高过膝盖的长统靴,偶尔化烟熏妆,狐媚而邪气。杂志编辑问她要照片配文发表,她狠心剪了自己的如瀑长发,懒做淑女,女人到了35岁,淑女装扮显老啦。短发烫成原子弹爆炸状,一根根刷成玉米黄,不近视,但一张小圆脸上架座欧亚大陆桥——水蜜桃色色玳瑁眼睛,时尚逼人,顺带遮掉因熬夜写作而早生多生的黑眼圈和鱼尾纹。依青苔班驳的老墙边拍照一张,电子邮箱发过去,编辑点开看,仿佛人间妖孽,被法海漏掉。总之,一切装扮往年轻妖艳的路子上放马奔驰,仿佛祭坛上她这样诚心摆上各类供品,再心念咒语不懈,年轻和才情便如神灵附身,且永不逝去。
看小区里大妈们天天泡电视剧,嗅觉灵敏,猛悟到中国即将进入老年社会,电视剧更会走俏,于是想到改行写小说,将来要玩影视剧。所以近来翻遍书橱,狠啃书本,耗到半夜睡下。阳历三月,怕夜起春寒,睡前紧紧捂了被子,一觉醒来,一头的汗。做了一个噩梦,梦中一条长蛇蜿蜒自身后追来,幽暗的色泽,左右躲不过,一路狂奔啊,前面大河挡道……醒了,摁亮床头灯,看看挂在墙上的钟,凌晨四点二十。老公也醒了,揉眼问她怎么了,她说做了一个噩梦,老公解了,告诉她,当心小人暗里使坏。不过一个梦,怎么可以当真呢。下午要去拜访德高望重的宋老,精神要足,于是灭了灯,继续睡。
老公的一只大手背后伸过来,缠缠绕绕上了她的身,摸——求欢啦。可是,可是,自己一点也不想。将老公的手拿开。老公是哪吒,至少有六只手,一只拿去,一只又来。“下午要出门的,不要了吧!”求老公了。不记得有多长时间了,她已经很烦做那件事,何况下午要出门,更不愿意了,总疑心那件事累人又不洁。“你就是不想!”老公怨道。“这个年龄应是虎狼下山,你呢?都是写东西害的,你们这些写东西的女人,写到后来,一个个都成了尼姑和道士。”老公很是愤慨指明这些反动派的下场。其实是名利害的,程想,不为名利,那么辛苦写干什么,完全可以无视稿债如山,可以把编辑的约稿函作垃圾处理。那么老规矩吧,伸出手摸笔,在枕头底下放着的夫妻帐薄上再记上一笔,欠欢一次,答应晚上定然向老公交待还清。至于陈帐老帐,往后延延罢——想想,从前,在床上,她不欠帐的,现在,总是欠。唉——到处都是欠帐,欠银行贷款,欠编辑稿子,欠老公鱼水之欢……
早上起来,洗个澡,忙家务,至九点半坐上电脑开工。同学魏小雅打来电话,说晚上有个小型同学聚会,嘱她要去。程未敢答应,想着晚上自宋老处回来,一定有不少材料要及时整理,远大理想急等实现呢,同学情谊暂时放放,程承认自己是个物质女人,什么时候都能从容地捍卫名利。《锦都晚报》的专栏稿要交了,写什么呢?簪子,文胸,旗袍,口红,胭脂……都已经写过。这次……头巾吧。于是,电脑旁她幻成天宫织女,十指纤纤,织出片片锦缎化作七彩云霞,飘向人间,由此,佳作出世,字字句句,浸透程氏的多情与粉艳,翌日与读者见面。文字面前,她总像是个正在恋爱着的女子,忧忧戚戚,乍欢乍喜,物皆着我之色,已经很少有人去戴的头巾,程替它作出一篇怨妇吟。
写完,靠椅子背上,闭眼,听一段昆曲,暂时放松。是青春版《牡丹亭》,杜丽娘已经是年轻的沈丰英来扮演,早先演杜丽娘的张继青现在已经极少露面,在台后了,现在若再上台,想应该是老旦了吧。没奈何,都要角色转换的。舞台不可能总是一个人的,所以,未雨绸缪最是明智。青春文学这一块玩不长,程为自己想到改行写长篇小说感到庆幸,下午去拜访宋老将是一个神圣的开始。
宋老家世背景复杂,他是父亲的小老婆养的,大老婆养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现在台湾,当年都是以国民党家眷身份在四九年大撤退时随父亲一道过去的。落下宋老和他母亲母子相依,建国那年,宋老才五岁,怕被作为反动派残余势力揪出来,隐姓埋名多年。文革时期却因为侮辱妇女的罪名而入狱,七八年平反出狱,进工厂,小官做到大官,直到到了省里。两岸实现“三通”,宋老兄弟团聚。程认识宋老,是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她作为青年代表发言讲话,他在台上目光灼灼看下来,看向她,如阳光普照幼苗。会后交谈,竟然都是老家在江北,又近了,于是互换名片,从此来往。
程想通过与宋老促膝长谈,以他为原型,写部小说。小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她不想把这次的写作当作练笔来试试,她没有时间来试。小说将以宋家三代悲欢离合为主线,穿插爱情与仇恨,再现时代风云变幻。相对于从前的豆腐块,这算是宏大叙事了吧。即时,文字的舞台上,她将由花旦平稳而辉煌过渡到青衣,乃至老旦,而不是江郎才尽如灯寂灭。
下午吃过饭,小睡,起床化了妆,开车去宋老家。噔噔噔,上了四楼,宋老已经开了门等在门口。“马蹄声碎!听到噔噔噔,就知道是你来啦,年轻人到底有活力啊!”未等程来问,宋老已替自己提前开门等候作了解释。然后将程引到书房,宋妈妈送了两杯茶进来,侍立赔笑一番,退身出去,赶着出门打麻将。
程跟宋老交了底,说自己准备涉足小说,并且久慕宋家三代不寻常的经历,想听他们家的故事。宋老好客气,说可以可以哦,只是你要常来,一次是说不完的哦。程终于放下心来,宋老是答应了,从此,她将能从宋老这里掘得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回去,用她程氏针法飞针走线地串起来,绣成锦缎,到时宋老再出面,煽风点火一宣传,必是一宏篇巨制铺向江北大地。程端起宋妈妈泡的茶喝起来,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子覆满一桌,桌上的茶花从浓厚的绿叶中开出深红的脸蛋来,仕女出游垄上踏青一般,一切欢喜,一切明媚。
宋老陪喝了几口茶,问她可爱收藏,程对收藏没兴趣,没耐心玩,也玩不起。一堆旧货,死尸一样的东西,老贵,想想,人们玩旧货,恋的怕还是旧货身上的一坨光阴吧。哎!又怕扫了宋老的兴致,于是折中说:玩不起,偶尔看看别人玩。宋老站起身在橱里掏,慢腾腾掏出一件件藏品,有民主将军张治中的一封亲笔信,有清康熙年间的一幅地图,宋老说,经鉴定,这是真品,这黄晕的颜色不是茶水黄,是真正年代久远空气氧化成的哦。于是程凑身过去,贴近那地图,装作兴味浓厚。宋老指给她看,说这西北角的某一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已经离婚改嫁沙俄了。觉得宋老话幽默,程扭头笑,竟看见宋老的另一只手什么时候已经搭在她的肩膀上。一阵尴尬。程赶紧走开,重提旧话,和宋老谈起宋家家史,宋老将地图折起来,在程额头拍了三拍,说不急不急,以后慢慢说。程想起孙悟空当年拜师学艺,师傅说不收他时却在他头上敲了三下,于是孙悟空夜半三更来到师傅房里,从此师傅传他七十二变的本事。这样想着,宋老已经又端出一件藏品,石头一块,人参化石。宋老指给她看,循循善诱,说,多像一个女人曼妙的身体,瞧下面,两节须根叉开,多像女人细长的大腿……程已经脸热起来。桌子上阳光灼灼,程感觉宋老的眼光也是灼灼看过来,令她无处藏身,竟有衣服被剥一般的羞愤。
“喜欢,就送给你吧!”宋老已经近前来。“不,不,我不喜欢的。”程赶紧拒绝。“不要紧张,也不要放不开,否则就太小气了哦,我喜欢和你们年轻人做朋友”宋老说,隔着一件春天的毛呢裙,程感觉她的屁股后面已经有一只大手摸索,正向着大腿方向转战。程的脸已经烫得像烤红薯的炉子,不敢看宋老的脸,心里是火山伴随地震。怎么办?一巴掌甩过去?甩过去能成英雄,但是她的鸿篇巨制将就此捐躯。闭上眼,任其践踏?怎么可以!在家里已经性冷淡,这会子更不可能卖身求文。
程知道下文将是什么,那么移开宋老的手,向他打欠条,就像早上和老公记欠帐一样。笑话!人家怎么可能答应,人到这把年纪,活成精了,就图现的,谁会相信你成名收利之后,记得还他一回。程知道这一点。
“哐啷——”门开了。彼此怔住,宋老收手,看向门外,是宋妈妈回来了。“怎么这时回来了?”宋老问宋妈妈,声音又低又硬,宋妈妈听不出来声音里强压的暴怒,一脸无辜和失望说是一起打麻将的张妈妈家里出事了,老头子在理发店里被抓起来,大约跟人家理发的姑娘有纠缠。宋老哦了一声,转身又走到橱边,不知道是要收东西还是掏东西。程这时才想起来要逃遁。
上了车,发现自己浑身发冷又发抖,想想不能开,怕出岔子。于是一个人在街上转,没有方向,心乱如麻,每一根麻上打满恨结。恨宋老,恨他那幽暗而布满陈腐之气的房间,甚至恨小说。不为小说,她的高过膝盖的长统靴才不会踏进宋老的虎穴。她想找一个人说说话,找谁呢?抬头看,大街上人潮滚滚,正是下班时间,城市像个醉鬼,物欲如酒流淌,伴同他早上把这些各具形色的人们吃进肚子里,现在,又把他们呕吐出来,散布到大街小巷。她想回家,跟老公说,说她心里好愤恨,说她的屁股今天被宋老隔裙摸过,若不是宋妈妈从天降下,难保今天要险些失身。但是,想想,不能回家,不能跟老公说,天知道老公会不会完全相信她的话,而不再作进一步联想。“就摸了屁股吗?真的是隔着裙子的?其它地方侥幸免过?”这样的话老公大概会问,不问也会藏在心里想。老公也许从此把她的屁股当作被沙俄占有的西北角领土,漠然的,不再碰它,不再将它视作是自己的领地。啊,自己已经冷淡,老公若要再冷淡,那她的婚姻将近如飘萍。想想后怕,更觉春天的黄昏有寒气浸人,于是拐进路边一家茶楼,像只孤舟暂时借岸一泊。
靠窗坐下来,继续想,迫切想找到一副耳朵,来听她控诉宋老是大坏蛋,是藏在墙缝里冷不防叮女人的大马蜂。这样的话最好找女人来说,而且也是玩文字的女人,才会有共鸣,那么找胡苗苗。电话打过去,半天才通,胡苗苗语气里不是很亲热,涌到喉咙门口的话于是咽了咽。想想自己这些年,风光总是盖过胡苗苗,也是招她嫉恨了吧。女人太优秀,合该遭同类诅咒,也许胡苗苗巴不得自己失了屁股乃至失身。于是寒暄一番,问她近来创作状态如何,然后装作无事般收线。花小丽更不敢打给她,那个大嘴婆,一定到处转播,然后版本变样,宋老将依然德高望重,只有她程锦如,写着狐媚文字的程锦如,一定在众人口中改判成勾引老同志的险恶巫女。一个烂球捧在手中,她想抛出去,总找不到人来接。“请问你需要什么?”服务员过来问。程收回思绪,看看服务员,说来杯干红吧,看看天色,又点了一份鸡堡饭。
饭吃得无滋味,干红喝掉,想再要一杯,又罢了,不敢将自己放醉,现在是孤身一人。何况屁股后面似乎总还有一只手,在那里摩挲来回,叫她浑身难受。窗外,路灯已经亮起来,马路上,有人行色匆匆,有人悠然踱步,再看,看见马路对面那位穿格子裙的女人真像同学魏小雅。呵,想起魏小雅的一桩旧事来,高三那年冬天晚自习,从艺术楼四楼下来,赶上楼梯灯坏掉,被好色的美术老师软拉硬拉牵着一路下了艺术楼,回来好恨,擦肥皂洗手,洗了十五分钟,成为笑柄。于是想起打电话给魏小雅,通了,那头西湖歌舞闹哄哄。魏小雅哗啦啦笑着,像一盆碗碟翻倒在地,唤程是只懂练功的李莫愁,问她大作可写好,愿不愿过来,程罢了,说听她声音已经感受到那边的快乐。这么多年的写作,已经将她训成长颈鹿,再遥远的枝头,稍稍踮踮脚,她都能勾到叶子们的青气。临收线,跟魏小雅说起当年被美术搀着下楼回来猛洗手的事,魏小雅说忘记好多年啦。啊,竟然忘了!程有点怅然。一个人又枯坐了半个钟头,然后释然——遗忘,应该是现代人最好的自我修复能力。将来,她也会忘掉今天的不快的。程这样想着,慢慢觉得粘在屁股后面的那只大手正结痂脱落。只是,今晚,她要找个树洞,把这个痂,把这个秘密掩埋。
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是的,一个鸿篇巨制在这样一个春天的夜晚提前变种为一篇叫做《内分泌失调》的东西。程在这个只有3000字的豆腐块里,像个巫婆诅咒:“这是一个内分泌失调的时代,当红青年女作家娇花一朵,在文字世界里来回奔突,如负大山,却久患性冷淡;德高望重的名流,苍颜白发,朽木一堆,却能倏然间于背后伸出淫手。”写完,打开邮箱,将小说发给新约稿的杂志编辑,这个下午的不堪将随这3000字一道烟消云散。桌子旁边的玻璃瓶里插着一根富贵竹,清水养竹,真是干净,程心里叹。想想下午宋老的那只手,若是按在经常与自己同版的80后艾儿和90后小氓的屁股上,将会怎样?世故的80后艾儿也许会默然无语,收了宋老的人参化石;张扬的90后小氓会甩过去一巴掌,然后对外广告,炒作成名。想起自己,什么都没要,她是清水养竹,剥开油彩满面,其实还是一根质朴而尊贵的植物。名和利经纬织就的物欲时代里,她这样惶惶穿过一劫,感到心安。
掏出手机看时间,呀,十条未接电话,都是老公打来的。忽然想起,下午拜访宋马蜂,将手机调成会议模式,到现在还没调整回来。还有短信几条,老公告诉她,记得要早回,早晨的欠帐不还也没关系,不要被累累债务吓着了不敢回家。程笑。没有回老公,倒是发了条短信给魏小雅:到家了吗?抱歉,今天没参加,我后悔啦!小雅回:躺在老公怀里啦,你呢?别只顾成名成家,要记得陪陪你老公喔!程又笑。
出茶楼找到车,慢慢开回家,一路上,青草的香气一阵阵刮进车里,想起恋爱时跟爱人在河畔的青草上偷欢,茅草凉凉的垫在腰下,河水呜呜低吟,和着虫鸣,月色似乳流淌……回去,要学习魏小雅擦肥皂,洗个干净,然后将早上记下的一笔欠帐狠狠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