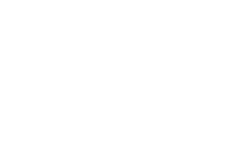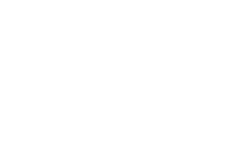一连好几日的晴天,气温慢慢地回升。和润的阳光,花园里消融的水,与几日前凛冽的北风,停留在到处的雪,似乎在季节的交替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在季节的交替里播放出不同的信号。就这样,一个冬天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一个春天也已经到来了。我还未来得及将流落在天水和临夏的那些细细碎碎的记忆串联成一个整体,缝补成一顶帽子,新年的结界就被时间的怨气冲破了一个洞,新年的装饰也被时间的剪刀剪去了一小块。
我真想把自己也分成两半,然后精心的打两个包。一个包送给昨天,一个包留个明天;一个包里存着旧年的回忆,一个包里揣着新年的祝福;一个包里我喜欢晴天,一个包里我喜欢阴天;一个包里是我的肉体,一个包里是我的灵魂。可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未免有些异想天开,更是白日做梦。正如你无法在镜子里同时看到自己的前面和后面,也无法同时在眼睛里看到事物的左面和右面。
生活里的种种,本来就是如此对立的存在,如此正反的辩证;自然里的种种,又何尝不是如此对立的存在,如此正反的辩证呢?我又何必去用执念划分一个界限,计算一个往返呢?当生活里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用热情去充实它,用脚步去经过它,而不会找不到漫漫的方向,也不会看不清匆匆的过客。
离开家的许多个日日夜夜里,只是在电话里和亲戚朋友相互关照着彼此的生活,也再电话里听爸爸妈妈诉说着村子里的变化,以及村子里人的变化。谁家的老人去世了,谁家的儿子结婚了,谁家和我一般大的已经结婚的儿子又有儿子了,谁家的那个人不小心吃亏了。这些都像是一个个一悲一喜的故事,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的我故乡那无字的画谱里大同小异的转放着,上演着,也变化着;亦如一颗颗脱落的门牙掉在了泥土里,多少年后再从泥土里滑溜出来,矗立成我们的墓碑,顺便也写上我们的故事。它们在消耗我们生命的同时,也在打磨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用一种简单的态度,简单的思维去看待前人的做法;也不再用简单的态度,简单的思维去揣测后人的做法。它们也是被用来铭记或忘却的,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悲痛欲绝。
而在家的这些日子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天都待在巷道里,忘记了吃饭,也遭受了爸妈的责备。以前喜欢着的兴趣爱好,也不再喜欢了,甚至还有些排斥心理。当然,偶尔也会出去转转,和村子里的人们交谈几句,回答着他们近似于福尔摩斯探案的疑问,仿佛要从蛛丝马迹里,剥落一张离家的面孔,再热情的给我换上一张那年的面孔。于是乎,一幅幅那年的场景便在他们和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盈。有我那年蹲在巷道里下象棋的身影,有我那年和玩伴一起掏鸟窝的身影,有我那年追赶一只猫的身影,有我那年背着书包上下学的身影。只是如今,这无数个身影合成了一个刚刚回家的我,至于我在外面的身影,是已经和他们没关的,是他们也没看到的。我不能去否认哪一个不是我,不能去承认哪一个又是我。存在过的东西,就算是时过境迁了,也会跟随着一阵阵用虚物或者实物呼啸而来的暖风,时不时吹过你的面颊,抚摸你的心灵,真真切切如一个拥抱,又依依稀稀似一场梦境。
离家和回家,也常常会带给我两种截然的心情。没有什么悲伤,也没有什么担忧,却增添了一点点未知的色彩和一点点陌生的感觉。就像有的人已经死了,可我还以为他活着;有的人还活着,可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有的人已经搬家了,可我还会去原来他家的位置寻找;有的人已经不种地了,可我还以为他还在种地;有的人还在种地,可我还以为他已经不种地了;记得原来有公交车站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公交车站;记得原来没有公交车站的地方,也已经有了公交车站。诸如此类的情形,在让我欣欣然于家乡行走的过程中,也潸潸然于自己行走的过程。我的脚步和家乡的脚步,或一前一后,或一左一右,或一南一北,或一东一西,相似的方式和相离的方向,再也无法追赶着翩跹在那年里的蝴蝶,再也无法垂钓着游动在那年里的鱼儿。恍惚梦里,我就像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失忆的客人,默默倾听着别人溯说自己的故事。我拍手叫好,也偷偷流泪。
离家和回家,也常常会让我奔波于两个地方之间,并且路过了无数个地方。那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村庄的名字,我并不甚明了,更无从去溯本追源。当途经我所熟悉的农村,当看到一个个佝偻的背影被时间挥刀刻画在那一方热土之上,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又仿佛走进了别人的家乡。每每这个时候,连几分相似,几分不似,和几分无奈,都可以让容颜沧桑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既是回归与叛离的完美交接,也是回归与叛离的相互斗争。我不想过早的去论断可能的结果,也不想过晚的去认可可能的成就,那就让一个过程,来揭开一个答案吧。
渐渐长大,渐渐用年龄的幅度去量夺事物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渐渐用经验的眼光去待见人情的冷暖度和承受度,我们也活得越来越小心翼翼,活得越来越中规中矩。慢慢地,不再敢用一步去跨过曾经需要两步的台阶,不再敢用自身去爬上曾经几下就能爬上的大树,也不再敢用曾经的办法去解决如今相似的问题,更不再敢像曾经一样去戏弄邻居家的小姑娘。我们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在乎别人的感受;我们害怕人情的亏欠,我们也害怕世故的炎凉。或许,我们并不是害怕,只是觉得那些是小孩子的生活,觉得那些是不属于我们的快乐。
远去的不是不属于我们,得到的也不是只属于我们,就像是一顿美味的饭菜,已经吃掉的部分,和还没有吃掉的部分。从冬季步入春季,形成的对比和释放的信号,也年年如重复一般的来去。而我未来得及迎送任何一个季节,任何一个月份,转眼间风景就次第开放着赤橙黄绿的色彩。在一个生命因此而沉睡,一个故事因此而苏醒的同时,另一个故事会因此而苏醒,另一个生命也会因此而沉睡。